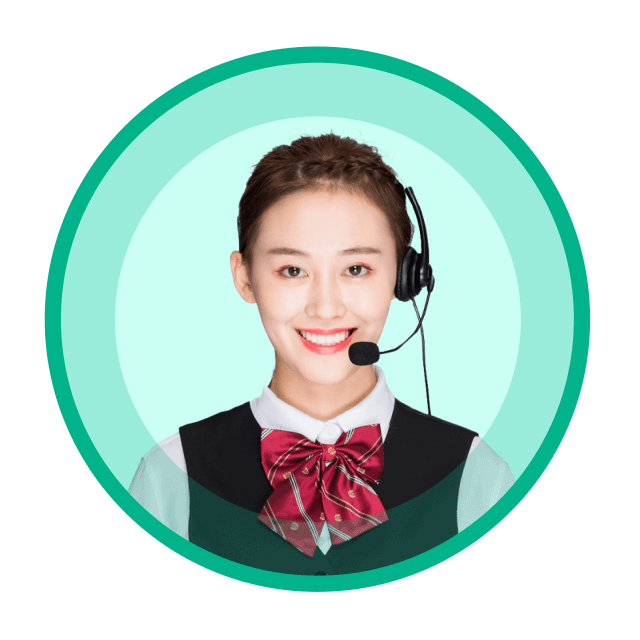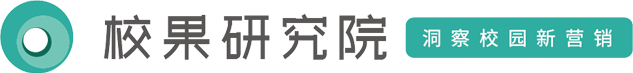00后是否还是“温和而焦虑”的年轻人?
2020年的钟声敲响,00后一代中,有人迎来了自己的20岁。
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三代,即便尚未踏入社会,他们已经被认为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体最富裕的一代人,不远的将来,他们也将成为中国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。
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,他们这一代人可能,温和,自负,或许仍有焦虑,但他们的身上好像唯独没有父辈年轻时惯有的忧伤——过去,代际创伤曾经在他们之前的几代人身上体现明显,但现在,一群不一样的年轻人正在走来。
“实现感不足”的中产
如果把即将在10年内整体踏入社会的00后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富裕的一代,这一结论应该是成立的,即便现在他们还没有真正拥有财富。
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认为,00后一代会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一支庞大的后备军。这首先源于,在过去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近二十年中,伴随房地产的货币化,他们的父辈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
家庭财富的积累,让00后成为经济发展间接的受益人。在中国家庭财富积累期间,没有房产税和遗产税,短期内这两大税种的推出仍需要时间,这使得00后一代不同于西方社会,他们没有折扣地继承了父辈乃至祖辈的财富。
在此之前,60后、70后作为中产阶层尚处于起步的阶段,依然有大批的农村人口或是体力劳动者,尚没有步入中产的状态,但伴随着几代家庭的脱贫,等到00后在未来10年踏入中产的阵营的时候,中国开始形成所谓的纺锤形社会结构,中产阶层的规模变得前所未有的庞大,现在,这样的形态正在清晰化。
张颐武认为,尽管这是生活相对优越的一批人,但他们的焦虑可能不可避免。他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,高等教育的回报溢价消失了,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了,还有一批拥有特殊技能的财富新贵(如演员、网红)甚至是富二代的崛起,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。
一方面,他们因为相对的富裕而敢于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,例如更加“任性”的职业选择,但另一方面,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外界不断的刺激。事实上,财产的继承是相对微薄的,这让现实生活和自我的期许形成了差距,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泛化,让这样的问题更为普遍。在中产阶层的生活得到基本的满足之后,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,再往上提升的难度开始加大。例如,事业上的成功、创造力的展开等,他们希望实现更高的目标,但这似乎并不那么简单。
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带来这一代人实现感的不足。
内卷化
和“富裕”同样重要的一个标签,是00后成长所处的互联网环境。如果说90后是互联网的第一代原住民,作为第二代原住民的00后,在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上,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前人。
最大一批00后出生的时候,是中国互联网开始高速成长的时期,他们从一出生就浸淫在互联网的环境中。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,中国兴起了诸多新型互联网的形态,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从某种程度上,互联网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方式,乃至培育了他们的品格。
新型的互联网形态和“古典时代”的互联网有所不同。如果将微博定义为“古典时代”的互联网形态,那么它的特点依然是集中式的、灌输式的,但新型互联网形态是分散式的、定制式的,同时它的呈现方式更富于感官的刺激:短视频创造的瞬间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,直播创造的氛围化的现场,这和原来仅仅依靠文字的初生代互联网很不一样。
张颐武认为,第二代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,在具备一定财富的前提之下,又亲身经历了中国新型互联网的发展,这共同造就了新一代年轻人日益“内卷化”的性格特点。
“内卷化”一词(involution),滥觞于哲学家康德,随后学者亚历山大·戈登怀瑟(Alexander Goldenweiser)借用该概念描述“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”。1963年,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·格尔茨(CliffordGeertz)在其《农业的内卷化(agricultural involution):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》一书中借用了“内卷化”的概念,即“一个既有的形态,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”,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“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,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”的过程。
中国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生态系统,给了两代互联网原住民提供一个完美的生活空间。几乎一切社会活动均可以在网络空间里发生和实现。
新型互联网平台让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扁平化,甚至线上消费都在进一步促成这样的扁平化:拼多多在三线以下城市乃至农村的普及,让小镇青年享受着和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的消费体验。抖音、快手这样的平台,甚至使得小镇青年也会通过个人的秀场来引导市场,而李佳琦的一场视频直播,能够让所有热爱口红的女孩们共同亲临一支口红试色的现场。
当消费市场足够庞大,年轻人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文化圈层,甚至,他们不再需要外来的精神偶像,让他们愿意付出大量金钱和精力的偶像,均将由本土来生产。
他们同时借由互联网找到了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归属。例如“饭圈”文化,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社交形态,“圈”提供了一种文化的想象,创造了一种同代人之间的联系,年轻人通过各自的圈找到自身的认同感。
这种饭圈文化可以很强烈,以至超出了一般的想象,例如对于偶像的运作,00后(或者可以早至95后)可以以很强的经济能力去付诸实践。这样的行为也拉开了他们和上一代人的距离。
张颐武认为,年轻人“内部”建立的这种联系,实际上已经让他们和上一代已经不再有什么联系。新的文化形态同时影响了他们的性格,和上一代人相比,他们也显得更加地感性。
不再忧伤
有意思的是,这可能是一群失落、焦虑、感性,但却并不那么“忧伤”的年轻人。
中国的代际创伤比其他文化要更普遍一些,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系,历史创伤导致了代际创伤,这在上几辈人的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。
张颐武认为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,因家庭财富积累而富裕起来的00后年轻人,同时也是互联网第二代原住民,他们见证并享受了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、低成本的服务以及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种种红利,这种红利带来的舒适度,不亚于甚至超越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体验,这些因素给他们带来了身份的自信、文化的自信和对国家的认同,同时,也带来了他们“实现感不足”却颇为温和的人生态度。
基于这样的一份认同,在70后和80后身上存在的“对西方的想象”在这里没有市场。
中国的新青年和新少年们,缺少亦或是无意于前人那样的忧伤——那种因东西方的差距以及自身无以施力带来的无奈和感慨。相反,他们带着生来的自负亦或是自信,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新的“感觉空间”。上一代人的忧伤,反而成为和他们难以取得沟通的一个方面。
张颐武认为,踏入社会的新青年们诚然也有自己的不快,但却不是依靠感伤的路径来表达:有时候,它可能表现为“发泄”,例如,“饭圈”之间的泄愤行为和言论。
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,令二者感到不悦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,令上一辈人感觉压抑的对象恰是下一代人生存的根基。张颐武认为,惯于感伤的70后或是80后,其本质更应该归结为产自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的观念。若以这一“类似自由主义的想象”来考察当下的中国的青年群体,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。
也因此,很难将这群新青年定义为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事实上,他们的温和面目,未必是基于精致的利己,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基本的认同。
张颐武认为,对中国最年轻的这一代来说,他们的确不再如前辈那样忧伤——一种更可能的情况是,他们会通过肖战这样的时下偶像来寻找认同和归属,并以此获得和中国的连接。
自信、自负、开放
内卷化以及温和的生活态度,并不能说明,00后们的眼界即是狭隘的。事实上,他们中的很多人,从很小就开始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视野。
新东方在2018年发布的《中国留学白皮书》勾勒了一副中国留学生的“画像”。白皮书显示,低龄化、目标多元化成为了趋势。在“留学意向产生时间分布—学生/家长”的统计中,家长对于小学阶段留学的意向已经达到了27%,中学阶段为29%,高中阶段为24%。
今年3月,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度国内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显示,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.21万人。出国留学人群更多地从中高等收入家庭拓展到中等收入家庭,也让自费留学人数占比逐渐增多。
在留学之外,00后也因家庭财力的支持拥有了比前人更早的跨国游历的经验,而这些恰给他们带来了身份和文化上的自信甚至是自负。
和二十年前走出国门的那一代人不同,新一代年轻人对于本国的依赖度正变得前所未有地高。甚至可以说,无论如何出走,他们可能已经注定离不开这片出生和成长的土地。
他们深度享受着中国在基础设施、消费、服务诸方面的便利,同时他们的生活已经与本国的新经济形态牢固绑定:他们既离不开微信,也离不开支付宝,甚至,离不开中国的某一个视频网站会员账户——因为大量的视频版权无法外溢,为了追一部作品,他们可能需要从外网再次“翻”回来。
正因为如此,这种被张颐武称为“高度的内卷”的性格特点并不妨碍他们在另一个层面上的“开放”。他们依然可以使用Twitter,可以使用Instagram。与此同时,本身高度内卷的中国经济和文化,也在试图外溢。
00后们有一天会突然发觉,一方面,中国经济的某些维度与全球高度地接轨和融合,但另一方面,中国创造出的一切,从经济底层到文化形态,又与外界形成了两条平行的路线。对他们来说,需要在这样的世界中调整自身认知的方向。